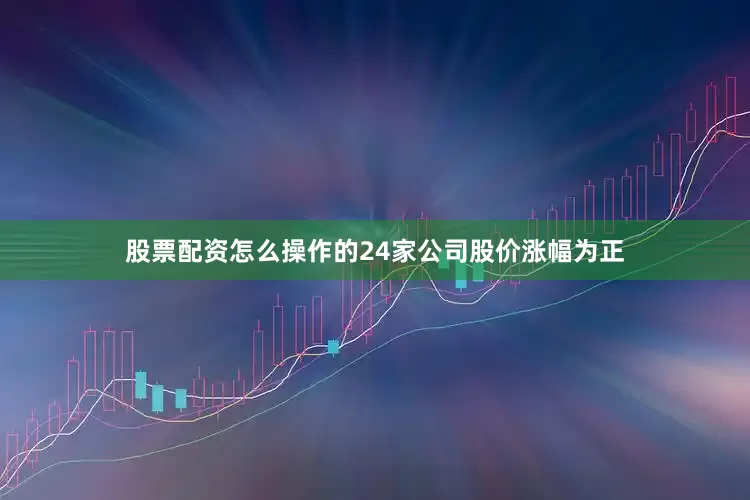1972年暮春时分,北越人民军以12万人,发起对南越和美国驻军的阮惠攻势(亦称春季攻势或复活节攻势),以求叩击历史之门。
一年后,随着美国的退出,越南战争也终于迎来了彻底的结束。

但事实上,若仅从军事角度来说,当时的南越和美国驻军在这一仗中的表现,并不算差。
那为何,美国在军事上赢得胜利的同时,却最终依旧无法阻止北越统一越南半岛呢?
时间还得拨回到1965年,当时的美国人刚刚介入越南战争。
然而最初,美国对于如何介入南北越的纷争,十分头疼。
甚至于,等到战争真正打响之时,美国佬一开始也只是象征性的派了部分部队于其中,而把更多精力用于,训练和武装南越阮文绍政权的军事力量。
只是随时间的发展,由于南越军队及其政府实在过于无能。美国才不得不增派更多的部队投入其中,并且严令其地面部队,不得越界深入北方,而主要依靠空军来对北越进行战略轰炸。
很大程度上,这一策略并不算差。毕竟当时离美国脱离朝鲜战争,也才没过去多少年,且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。
而越南半岛本身的地形,又足够复杂。故而,美国人无心将地面部队,投入到其中去消耗。
这并不单单是说,有没有能力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,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,这样做的必要性和成本无法计量。
于是乎,也就在这种大背景下,美军对越的首任司令,威廉·威斯特摩兰,一度将美军的战略定位为搜索与摧毁(Search and Destroy)。亦或者说,通过杀伤比来赢得优势。

可以说,这一构想基于消耗战理论:即通过大规模野战和火力优势,来歼灭北越军(NVA)及越共(VC)主力。
其中一个典型战例,是1967年的铁三角战役(Operation Cedar Falls)。在该战役中,美军以10倍于敌的伤亡比,摧毁越共基地,印证其以战损换时间的逻辑。

然而,该战略存在致命缺陷:因为它过度依赖装备优势,导致机动性不足,且忽视了对南越乡村的实际控制。
而就在1968年前后,威斯特摩兰刚刚宣称完,越共已丧失大规模进攻能力的时候。
该年开春,北越便以30万大军发起春节攻势(Tet Offensive),其突袭南越全境,虽未获全功,但却使得整个南越和华府的脸上,都很不好看。

也正因为此,威斯特摩兰被迫离任。而其后继者,克赖顿·艾布拉姆斯则换了与其完全不同的一套策略。

老艾此时的策略调整为,重点保护南越地区的人口密集区,并结合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,兵员日渐减少的现状,改以小型机动部队来取代大兵团作战行动。
在这一期间,除了美军的LRRP长距侦察队外,美国的其他诸如MSF等等部队,也表现得非常活跃。
与此同时,相比于摩兰,艾布拉姆斯此时还有一个任务,那就是要逐渐将美军撤出越南这个泥沼地,而将拱卫政权的任务,交由南越政府自身去承担。
毕竟在前面些年中,南越阮文绍集团所表现出来的腐败,实在太不让人放心了。
然而,正是因为艾布拉姆斯的这一举措,导致美军在1969年后的兵力骤减。
至1971年年底,原有高达50万的驻越美军,被消减得仅剩不到9万人(亦有说15万人)。
而到1972年3月,越军正式发起攻势前,整个驻越的美军已不足7万。
由此,便激发了北越,决战时机已至的念头。

另外,这里面还有一个较少提及的因素是。此时,北越方面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情报,明确得知美国该年不准备在越南继续投入兵力的红线。
而与此同时,中美关系开始趋向缓和,这就使得北越担心,中国有可能在其后减少对其的军事援助。
再有一点是,北越方面的军事指挥官黎仲迅,他敏锐发现接壤地区的南越第五师,其兵力不过1.5万人,却被分散驻守在三个省。
而其平隆省的核心枢纽安禄地区,虽然人口不到8万人,却由13号公路贯穿,而直通西贡。

更关键是,切断这条公路可使驻扎禄宁(Lộc Ninh)的越南共和国军第五师陷入孤立。
可以说,尽管这种选择,违背了北越传统争取民众的战术逻辑,但恰又因如此,使得北越军的行动变得更具有突然性。

与之相对的,南越第五师的指挥官黎文兴(也译黎文鸿),事实上对于北越可能的进攻已有所预见。故而在进攻前,他把其师指挥部转移到了安禄地区。

但跟南越方面表现不同的是,美军此时的军事顾问,如上校威廉米勒等人则认为,北越方面并不具备大规模的进攻能力。

很有意思的是,这倒并非是美军在战前,没有收到相关情报。而是当时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,主要依赖于美国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,进行情报传递。

而当时,南越军诸如第一战区司令黄春览等人,又过于优柔寡断。以至于等情报经由太平洋舰队,再到西贡总部和越军前线指挥手中时,其时效性已经大打折扣。

再一个,就是南越军也在调整。为此,它的指挥关系尚没有理顺。诸如南越陆军和其陆战队147旅等等,隶属关系就异常混乱。
白话讲,就是指挥不动,而作为本应为此负责的上级(第一军),更对此视若无睹。
最后,在西贡的美军总部,对于人工情报和技侦手段并没有结合来印证。
以至于,当北越在胡志明小道等地,多次出现传感器活跃异常的时候,美军竟然轻率的误以为,不会发生大规模进攻。
这就很奇怪了
难道美国人不知道,无线电静默的吗????
那么,在1972年复活节攻势中,北越的军事计划和作战序列,究竟是怎样的呢?
战役部署上 ,越军攻势按地理轴向分三路展开,每路均为合同战役集群:
1.北部战线(广治方向):以第304、308步兵师搭配第202装甲旅强攻DMZ非军事区,并突破南越第3师防线。

2.中部高地(昆嵩方向):以第320A步兵师与第203装甲旅穿插中央高地,切割南越第2军的防区。
3. 南部矛头(安禄方向):以第5、7、9步兵师,协同第201装甲旅直指南越首都圈门户,形成三面合围。
其主战兵力,按如下架构编成
装甲突击集群:以苏制T54主战坦克构成矛头,通过苏联紧急交付的重型坦克和装甲车辆,配属超过120个营,以实现装甲的集中运用。

不过需要说明是,这些坦克营与独立装甲单位,均属首次尝试步坦协同战术。
在初期,尽管因操作生疏导致作战混乱(如Lam Son 719行动中的协同失败),但经3000名北越军人在赴苏接受专项训练后,仍形成了基础的战斗力。
炮兵压制群:配备新型M46 130mm加农炮的单位构成火力核心,其27.5公里射程远超美军M101榴弹炮(11公里),为攻城提供了巨大的火力优势。

而由苏制83式萨格尔反坦克导弹,与反直升机导弹单位协同编组,以形成立体的反装甲和防空网络。

机动步兵师:第320A步兵师担任战役主轴,搭配第24B、第27、第271步兵团组成重装步兵集群。每个师级单位配属坦克营、炮兵营及摩托化运输营,以实现机械化突击能力。
防空保障群:以SA7防空导弹连与37mm高炮群组成防空屏障,有效遏制南越空军A37攻击机低空突袭。
后勤方面
战略运输网:北越人在战役前,接收到约2,000辆新卡车与10,000吨燃油构筑物资通道,并通过胡志明小道,实现师级单位的持续作战补给。
地方作战单元:北越共有9个地方营与44个独立连,承担侧翼掩护及补给线防御,填补正规军的空隙。
值得注意的是,北越此作战序列的建立,完全依赖中苏的战略输血。在1971到1972年间,北越先后获得价值15亿美元的军备,包括T54坦克、130mm火炮等重装备,使北越首次具备战役级的装甲突击能力。

但应当说,尽管此次越军兵力规模空前庞大,技术装备也远比之前的几次攻势都更强大。但其机械化的表象下,仍存在致命缺陷。
那就是,北越的指挥体系同样僵化,这导致各兵种难以实时协同,后来的安禄战役中,北越坦克与步兵脱节便是明证。
那么,开战前夕的南越和美国方面的作战序列、驻防分布又是怎样的呢?
首先,南越方面,尽管情报显示北越可能在二区(MR2)的中央高地发动主攻。但南越仍将最精锐的第1师、伞兵师和海军陆战师(总兵力约3万人)集中在广治省(Quang Tri)至顺化(Hue)的北部防线。

这种部署基于传统认知,北越一贯试图切断南越的腰部地区。而讽刺的是,北越此次为将矛头直指兵力密度最高的MR1,投入了17个步兵团、3个炮兵团及2个装甲团的机械化部队,这完全出乎南越的预料。
具体作战序列上
南越共设有三个军区,其中
第一军区(一战区)北部防线,下辖:
第3步兵师防区:广治省非军事区前沿
详细序列:第2步兵团(原属第1师精锐)、第56步兵团(含51团4营改编单位)、第57步兵团(含第2师6团2营)、附属第20装甲骑兵中队(兵力不足)。
特点:新组建部队,缺乏协同训练,指挥混乱;负责卡罗尔营地、梅禄等关键据点。

第1步兵师防区:承天省顺化城防线
详细序列:主力步兵团(番号未详、)附属地方武装及预备队。任务:阻击北越324B师对顺化的西翼进攻。
海军陆战旅:驻梅禄基地第147旅、驻南希火力基地第258旅
归属问题:名义隶属第3师,实际由军区直控,导致指挥脱节。
第三军区安禄方向,下辖:
第5步兵师防区:安禄省首府
增援部队:别动军2个营(4月7日)、第21师部分步兵营(4月10-11日)

第21师原防区:湄公河三角洲
临时调遣:与第9师协同防守忠诚营地,后奉命驰援安禄战场,但不适应丛林地形。
第25师防区:西宁省
状态:遭北越孤立,未能支援安禄主战场。
第二军区,下辖:
第22步兵师防区:昆嵩省坛灿、达苏基地
第23步兵师防区:昆嵩市

战略预备队及关键调整
空降部队:第2、3空降旅:原属总预备队,后期调往顺化支援。
别动军第1突击队:参与顺化防御战,受美军特种训练。
海军陆战师:广治反击战主力(6月),在美直升机中队支援下夺回广治市。
值得注意的是,此时的南越师级单位,普遍受限于地域熟悉度,例如第3师虽含精锐单位(如原第1师第2团),但新兵多且指挥混乱。
而海军陆战队,则因为归属权模糊。一度导致黄春览与第3师长巫文解的命令,相互冲突。
相比之下,至1972年初,美军地面部队仅存顾问小组(MAAG)和联络分队(LNO),总人数不足千人。其空中力量成为关键支柱。

但事实上,直到战斗打响后,美国第七舰队才紧急调遣小鹰号(Kitty Hawk)、星座号(Constellation)、汉考克号(Hancock)航母进入南海,并随后增派中途岛号,使其战术飞机数量在4月暴涨至130架。
而海军方面亦同时部署,纽波特纽斯号(Newport News)重巡洋舰等舰艇提供舰炮支援,尤其弥补雨季恶劣天气下的火力空白。
但在目前,说这些都为时尚早。
具体到,双方当时的兵力比和装备上面。
兵力方面:北越共计出动12万人,尤其在主攻方向,约为35,000人对阵南越的15,000人。
装甲力量:北越方面投入至少300辆坦克,其主力为苏制T54中型坦克(占比约53%),并辅以PT76两栖坦克及老式的T34。
具体分布如下
广治方向:308师、304师及3个独立团(第27、31、126特工团)配属坦克集群。

昆嵩方向:第203坦克团(含T54)协同第320师、第2师。

安禄方向:第5师、第9师配备独立坦克单位。
型号方面,北越坦克部队主要装备苏制T54/55中型坦克,及PT76两栖坦克。其中,T54承担正面攻坚,PT76则利用水道迂回。
与此同时,承继苏军的北越人,在该战役中将坦克集群进行集中使用(如昆嵩方向单日就投入了40辆T54),这一度得以突破南越的薄弱防线。
南越的装甲部队构成则为:
广治战区:第20装甲骑兵中队(M41轻型坦克+M113装甲车)
昆嵩战区:2个装甲骑兵中队(M41为主)配属第23师。
战略预备队:第3装甲旅分散支援各战线。
南越的装甲主力为M41轻型坦克(36吨,76mm主炮),其部署于安禄防线的第5师装甲骑兵中队。
该坦克正面装甲仅25mm,面对北越T54(100mm装甲+100mm主炮)和PT76两栖坦克时,生存率极低。

在战役初期,M41在洛宁(Loc Ninh)的反冲击中遭北越萨格尔反坦克导弹精准猎杀,暴露出机动防护与火力的全面劣势。
总体上,南越的装甲总量不足北越1/3,但精确数字尚无从得知。而根据南越装甲中队的编制17辆计算,且整个战役期间亦无整建制的覆灭记录。
故估计,其总量约为100辆。但南越非常缺乏重型坦克,主要依赖M41的76mm炮来进行反装甲。
炮兵方面
北越炮兵,按估算大致有超过500门,其具体如下:
北越炮兵大量装备苏系130mm加农炮和122mm火箭炮。被北越视为革命性新装备。

前者射程达27公里,精度显著优于此前装备的122mm火炮,可直接压制南越军的前沿基地。
同时,北越的炮兵优势,还体现在战役突然性上。比如其122mm火炮在攻势首日,即摧毁南越前沿通信节点,致使南越第3师的两个团,几乎瞬间丧失了指挥。

而南越方面的炮兵,按三个军区估算,最少也应有超过200门各型火炮。与此同时,南越方面还有得到了,来自美国的海军舰船火力提供支援。
陆军炮兵:南越的师属炮兵,以美制牵引式榴弹炮为核心,其M101型105mm榴弹炮:射程11km,部署于安禄外围火力点,每个炮兵连标准编制4门。但因阵地频繁转移,其难以形成有效的火力密度。

再有就是M114型155mm榴弹炮:射程14km,第5师在禄宁(Loc Ninh)前沿配置2门,用于远程压制北越集结地。
不过,综合来看,南越的炮位缺乏反炮兵雷达支援,在面对北越炮兵(122mm火箭炮+130mm加农炮)的饱和打击时,往往反应滞后。
海军炮火:美军3艘巡洋舰+38艘驱逐舰提供舰炮支援,最远覆盖至内陆30公里。
防空体系方面:
北越部署23/37毫米高炮,以及SA7形成立体防空网,迫使南越直升机在战役初期,难以进入战区。而南越方面,则不存在制空权问题。

与此同时,当美军参战后,其B52轰炸机执行2,724架次任务,投放7.5万吨弹药;战术飞机更日均达300架次。
客观讲,南越虽火力投射总量占优(18,000架次空中支援),但反应迟滞:广治失守后美军舰炮才抵达,且师属炮兵因指挥混乱,常遭反炮压制。
这种失衡,最终导致南越丢失就超过的10%领土,而北越方面则因为技术装备损失过大(装甲力量折损70%),亦无力扩大战果。
轻武器方面,南北两越就各自半斤八两了。比较值得一提的倒是,南越军队在连排级的机枪火力配属上,主要依靠美军的M60通用机枪和M1919A6 .30机枪,这相比苏军的PKM系列来说,其实是要略逊一筹的。
当然,必须说明。
这是帝林我个人观点。
接下来,我们详细说下,1972年北越复活节攻势的具体战斗经过。
其总体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第一阶段:全线突破与战略佯动 (1972年3月30日4月初)
在安禄方向,这是北越投入兵力最雄厚、目标最野心的一路。其由黎文甲中将指挥的北越B2前线司令部,集结了相当于一个军级兵团的兵力。

这包括第5、7、9步兵师(每师约万人)、第69炮兵师(装备122mm榴弹炮、140mm火箭炮)、第203坦克团(装备T54/59坦克、PT76两栖坦克)及独立步兵团、高炮部队等,总兵力高达约3.5万人。
他们的目标,是直指南越第三军区的腹地,即人口稀少但扼守13号公路(直通西贡的生命线)的平隆省(Binh Long)。
据解密的《B-2战区作战计划》,其命第五师攻禄宁、第九师取安禄、第七师穿插切断公路,三路需在5-10日内达成目标。

最终,进攻于3月30日拂晓前突然发起。而作为牵制和佯攻,北越第24、271独立步兵团,亦率先猛烈攻击临近的西宁省(Tay Ninh) 省会。

此举最终成功吸引了南越第三军区司令,阮文明中将和美军顾问的注意力,使后者误判北越的主攻方向,仍是传统的西宁人口中心区。
与之几乎同时发生的是,北越第5步兵师在坦克(第203团)支援下,猛攻平隆省北部重镇禄宁(Loc Ninh)。

当坦克出现在安禄城郊时,南越第九团的反坦克小组发现,他们的M72火箭筒,根本无法击穿T-54的前装甲。

于是,南越军遂崩。
相比而言,美军顾问威廉·米勒上校的战场报告,则向我们展示了更准确的细节:5时30分,教堂尖顶方向出现金属反光,接着我们看见炮塔编号271。
此时的第七师,已卡死莱溪至安禄的公路,而第五师残部则被分割在五个孤立据点。
随后,驻守此地的南越第5师第9团(约2个营兵力)在绝对优势的炮火和装甲突击下,防线迅速瓦解。
禄宁于4月4日陷落。
而占领禄宁,就等于切断了安禄(An Loc)北面的重要支撑点。
与之相对的是,北越第7步兵师的任务是,快速穿插至安禄以南的13号公路地段。
他们成功达成目标,并在安禄与南越第5师总部所在地莱溪(Lai Khe)之间,建立了坚固的封锁线。这意味着,安禄城在战役一开始,就被从陆地上彻底孤立了。

紧接着,北越第9步兵师从柬埔寨边境方向,在坦克和猛烈炮火支援下,直扑平隆省省会。这也是此役核心目标之一,安禄(An Loc)。
战役的焦点,几乎瞬间被转移到这座小城中。
不过,在正式介绍安禄之战前,我们还需要说下广治方面的战斗。此地在在北越的攻势规划中,是另一个重点方向。
该处的北越部队在安禄打响的同时,跨过非军事区(DMZ)和溪山地区,向南越最北部的广治省(Quang Tri)发动大规模进攻。
在这里,北越投入了数量可观的坦克(T54)和远程重炮。南越第3师在这突如其来的装甲洪流和压倒性炮击下迅速崩溃,广治省北部防线土崩瓦解。北越部队快速向省会广治市推进。

与此同时,在北越中部高地的攻击昆嵩/波来古同样迅猛。北越部队从柬埔寨境内出击,虽然未能像I、II战区方向那样取得快速突破。但其攻势有效地牵制了南越第二军区的预备队,使其无法增援其他两个方向。

第二阶段:安禄绞肉机与僵持 (1972年4月5月初)
安禄迅速成为整个攻势中最惨烈、最具象征意义的战场。北越第9师在第203坦克团和占绝对优势的炮兵支援下,对这座被孤立的城市,发动了一波接一波的步坦协同突击。

其攻势在4月12日达到顶点时,战场出现戏剧性转折:北越第九师三个步兵团突入安禄城区,却因坦克陷在瓦砾中,而遭陶式导弹猎杀。
但此时,北越的第七师已在南线构筑反坦克壕——他们用DKB挖掘机一夜之间,竟挖出三公里的障碍带,成功阻止了南越第21师的装甲救援纵队。
4月13日左右,北越的坦克甚至一度冲入安禄市中心。但南越守军,即主要由南越第5师第7团、第8团残部、第3伞兵旅、地方部队(RF/PF)以及临时拼凑的特遣队52组成的南越军,则殊死抵抗。
此刻,无论从人数还是火力上,当地的南越军队均处绝对劣势。他们的生存严重依赖两点。
一是美军的空中力量,当时美国空军和南越空军(VNAF)的战术飞机(F4鬼怪、A37蜻蜓等)以及至关重要的B52战略轰炸机,对安禄周围暴露的北越部队集结地、炮兵阵地和装甲纵队,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强度轰炸。

第二则是,美军紧急向安禄守军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陶氏反坦克导弹。这种武器在对抗北越T54坦克时表现出色,成为守军对抗装甲洪流的救命稻草。

也正因为此,安禄的攻防演最终变成了残酷的消耗战。北越的炮兵(尤其是射程极远的130mm加农炮)日夜不停地轰击城内,造成巨大破坏和伤亡。
同时,北越军还大量派出步兵,在坦克掩护下反复冲击南越阵地,而南越守军则依托建筑物、工事残骸和空中支援死守。
城市内遍布废墟,战斗经常是逐屋逐屋的展开,近似于重演了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。
这期间,北越也曾试图切断守军空投补给线的努力(使用SA7防空导弹攻击低空飞行的运输机)。
但尽管他们获得了部分成功,却并未能完全阻止美军的空中补给。
与之相对应的是,北越部队于5月1日最终攻陷了广治市,这是整个战争中北越攻占的唯一一个南越省会城市。此地的南越部队,随后退守至顺化外围的香江防线。

而昆嵩的北越军,在中央高地的攻势,虽未取得省会级突破,但依旧形成了巨大压力,并继续在昆嵩外围与南越军队形成僵持。
第三阶段:转折与北越攻势衰竭 (1972年5月中9月)
时间进入5月,持续猛攻安禄的北越第9师等部队。在经历了惨重伤亡(尤其是装甲部队在空袭和TOW导弹打击下损失惨重)和后勤补给困难后,进攻锐气明显下降。
5月11日,战局逆转的关键在情报破译:美军监听站截获了北越第275团电文弹药基数仅剩0.2,霍林斯沃斯中将于是立即出动B-52机群,为其再添上一把火。
据《第三军作战日志》记载,5月12日,美军的轰炸在城西消灭了至少约200人。
但北越工兵仍在炮击间隙,修复了禄宁至安禄的输油管道——这条藏在红土下的钢铁血管,每小时为前线输送3吨燃料,保障了北越军坦克最后的冲锋。
于是乎,南越第5师得以在师长黎文鸿准将指挥下,在美军强大空中支援的绝对保障下,继续依托城内残存阵地顽强固守。

5月中旬,南越发动代号为Song Than(台风)的反击行动,试图从莱溪沿13号公路向北,打通前往安禄的道路。
虽然其地面推进极其缓慢,且代价高昂,但此举仍象征着北越彻底攻占安禄的企图,已告失败。
到5月底,安禄之围虽未完全解除,但北越业已无力,再发动有效的决定性攻势,战场主动权开始易手。
而尼克松政府为了挽救南越政权,并逼迫北越回到谈判桌,亦下令发动代号为Linebacker I的战役。
此时,美军海空军对北越本土的港口(尤其是海防港)、铁路枢纽、油库、电厂等战略目标进行了大规模高强度的轰炸,并首次在北越港口布设水雷,切断了苏联、中国经海路对北越的军事补给线。
这在很大程度上,极大地限制了北越,维持其前线庞大部队持续作战的能力。
同时在南越战场,美军B52和战术空军对北越进攻部队的打击力度,亦有增无减。
随着雨季的到来(严重影响北越后勤和机动)、美军战略轰炸对补给线的致命打击、以及在南越战场(尤其是安禄和随后南越在广治的反攻)遭受的巨大人员和装备损失,北越的复活节攻势,最终在1972年9月左右基本停止。
事后来看,设若南越在战役初期采取弹性防御,而非固守城区。兵以炮兵集群配合机动部队实施诱敌深入,或可规避坦克集群的正面冲击。
此乃借鉴《武经七书·吴子》以车制骑之法,即当T-54在水网稻田中机动受限之时,若以M113搭载反坦克导弹实施侧击,或能扭转装甲劣势。
但历史不容假设,南越指挥层的阵地依赖症,终究使其重蹈法国在奠边府的覆辙。
战役的最终:北越承认损失坦克120辆、兵员2.5万人,南越则阵亡8000人(含1000平民),安禄城区更仅剩6座建筑幸存。
但就双方深层战略意图来说,却耐人寻味:北越虽未攻克安禄,毕竟达成了以战逼和的政治目标——因为最终它还是迫使了,美国在巴黎和谈中的让步。
而南越人虽然守住阵地,却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,其正规军第21师在解围时折损过半,更暴露了南越机动部队的脆弱性。
某种意义上,这也预示了一年后,南越政权的最终败亡。
战后评点
北越以14个师、26个独立团的规模发动攻势,企图通过占领南越北部四省(约10%国土)+摧毁南越军有生力量,来迫使美国放弃其越南化政策。

其战略构想延续了《孙子兵法》上兵伐谋的思维,却忽视了关键变量:南越军已装备M113装甲车、F-5战斗机等现代化武器,其火力配置已属第三世界强军标准(1972年南越军军费占GDP的18%,装备美制坦克400余辆)。而北越则仍依赖于,通过T-34/54坦克与步兵冲锋的传统组合。
与此同时,美军第七航空队日均出动2000架次空袭(如后卫行动中投下15万吨炸弹),造成北越装甲部队达70%损失(134辆T-54、56辆PT-76)。
这种空中遮断战术,复刻了1944年盟军对德军的运输战模式——当北越部队在广治省推进时,其后勤线经常被B-52的地毯式轰炸所切断。最终导致,北越前线近10万人的兵力中,有30%因缺粮缺水,而丧失了战斗力。
(帝林:老美事后的评估)
再一点是,北越指挥官普遍较为愚钝。当战线僵持时,他们习惯性的延续既往的条令。
这或许是1968年的春节攻势中,北越军普遍伤亡亦很大,导致新一代的军官,更多接受的是来自苏联教官的培训,而鲜少有机会去进行实践。
于是,他们一再地犯与1916年索姆河战役中,德军相似的错误:即试图以密集冲锋,来夺取预设阵地。
比如在安禄战役中,北越第3师以3000人伤亡代价仅推进2公里,其伤亡比(1:5)远超美军标准。
(帝林;但话说回来,越军能持续如此进攻,亦说明其军队的纪律的凝聚能力)
更致命的是,北越军队始终未利用南越军防线西翼(柬埔寨边境)的薄弱点实施战略迂回,反而一再强攻岘港等美军火力覆盖区,这可能得算其最大败笔。
这换是当时中国方面的指挥官,则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。毕竟自PLA建军以来,就十分善于和喜欢战略迂回。
当然了,客观来说,1972年北越春季攻势的军事行动,是与巴黎和谈的政治博弈同时进行的。
其本质,既是工业文明军事技术(美军空中优势)与农业文明(人海战术)的冲突,亦是越南化政策下,南越政权纸糊国防的结构性暴露。
克劳塞维茨在《战争论》中强调,战争是政治的延续,此战的终局恰证明:当军事手段无法突破技术代差,所形成的火力壁垒时,政治谈判必然成为双方止损的唯一通道。
(帝林:@普丁)
而富勒在《战争指导》中亦指出:现代战争的胜利,属于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的一方。
综上,1973年《巴黎协定》的签署,本质就是美军用空中优势威慑,换取了最后还算体面的撤军。
而北越则是用有限的占领,巩固就其革命成果,并最终促成了南越政治上的败亡。

可以说,此战验证了一个军事真理:当一方掌握绝对制空权时,地面攻势的意义已从领土征服退化为谈判筹码——正如1945年日军在本土的决战叫嚣,本质亦不过是用军事姿态,来换取投降条件的政治表演罢了。
安联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