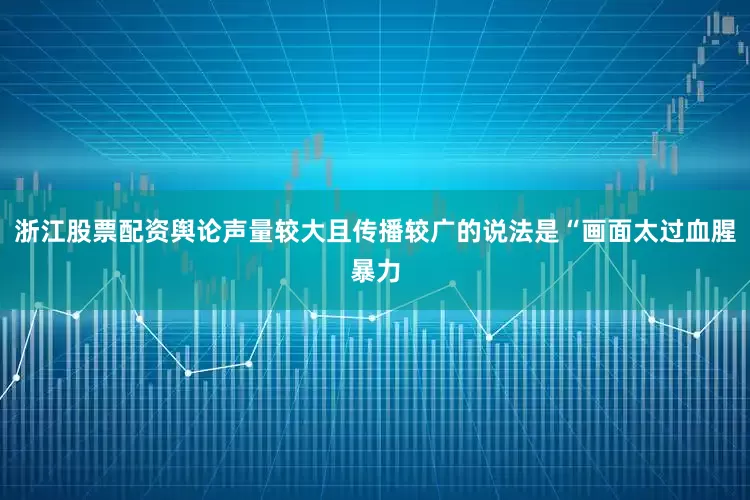五次演绎毛泽东,王仁君在历史暗夜中寻找火种
军博的秋天,院子里有几棵老槐树,叶子落了一地。那天下午,王仁君站在土地革命战争馆门口,有点发愣。他手里还攥着一张当年学校组织参观时的小票根——1996年印的,如今纸都泛黄了。这些年,他总觉得自己跟这片地方、跟某个名字,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。

人群散去后,他独自溜达到《秋收起义》的油画前。画里的红旗斜斜插在泥土上,有点歪,但很倔强。他想起小时候奶奶讲过:湘潭那边流传一句顺口溜,“稻谷熟了要快割,人走正路莫回头。”她说毛家屋场的人都是犟脾气,不服输。
其实从《古田军号》到《浴血荣光》,五次扮演毛泽东,每一次都是新折腾。36岁第一次“碰面”,恰好是古田会议上的毛泽东;42岁再遇,又赶上遵义会议时期,两人的年龄卡得死死的。有时候他会开玩笑:“可能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吧。”

剧组拍戏最怕真冷、真饿、真累,可导演陈力偏偏喜欢“来真的”。他们下乡去闽西革命老区踩景,那些小村巷子弯弯绕绕,一进屋就是灰尘和蛛网。有一回,为了拍阁楼里的密谋场景,王仁君差点把44码的大脚卡楼梯缝里。“你别看我现在能蹦跶,当年主席估计比我还难受,”他说,“三分之二脚掌悬空,我要是真摔下去,这段历史就穿帮了。”
这些琐碎细节,也不是瞎编。在江西瑞金还有位姓钟的大爷,说他祖父年轻时给红军送饭,看见过主席拂蜘蛛网,一边嘀咕:“唉,这房子比韶山冲潮湿多咧。”大爷记忆力好,把这些事念叨给外孙听,说是“真人干实事”。

每部戏开机前,都得先掉肉。《浴血荣光》刚定妆时,他瘦到腮帮都凹进去,只为贴近史料里那个疟疾缠身、“皮包骨”的形象。“减肥这种事儿,不止女演员懂,我们男演员也有苦水。”但更难的是心里的转变:从追随者,到探索者,再到领袖,每一步都踩着刀尖跳舞。
有一场戏,是杨开慧托人捎鞋。包袱打开的一瞬间,那股幸福劲儿,就像冬天突然摸到热水袋。他穿上鞋傻乐半天,还偷偷吃醋:“咋写信净提何长工?”生活气息全靠这些小动作撑起来。不然角色只剩高大全,看着也没啥意思。

情感这东西,很怪。在行军路上谈及妹妹牺牲,要哭不能哭,要忍又忍不住。导演提醒他:“你是主心骨,在战士面前不能垮下来。”于是只能憋着,把悲伤埋进嗓眼,让观众自己体会。这招挺绝,比嚎啕大哭管用多了。
至于那些所谓伟人形象,其实底色全在人味儿。一位湖南长沙的老人曾经说过,他们小时候听自家亲戚讲,“润之哥”年轻时爱逞能,经常河边游泳比赛输了还嘴硬,说什么“我是仰泳派”。这种霸蛮劲,被王仁君学得惟妙惟肖。《问苍茫》拍游泳镜头,他练习仰泳半年,就是为了一个镜头能飘出湖南味道来。

对话语调也考究。“莫要做”“你晓得伐”,普通话夹杂韶山腔,让角色更接地气。据说早期党内会议记录残存的一份速记稿,上面标注某领导讲话频繁出现方言词汇,还被同僚私下打趣“不够国际范”。可就是这种原生态语言,更容易让屏幕外的人生出亲切感。
史料翻烂不少,可真正让他动容的是1931年的一个传闻。当时赣南兴国县流行一句民谣:“石板桥头摆龙门阵,大伙齐心闹革命。”据当地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,那一年主席常带兵驻扎石板桥附近,每晚与农户围炉夜聊,被孩子们叫作“大个子的故事佬”。这一段后来没法搬进剧本,但成了王仁君揣摩人物性格的小秘密——领袖也是普通人,会讲鬼故事哄娃睡觉,也会深夜独坐发呆数星星。

每次饰演结束,总需要时间抽离出来。有时候躺床上一闭眼,全是台词和文稿乱飞。他媳妇调侃他入戏太深,还拿笔模仿他的书法练字,说写出来像鸡爪抓地似的。但只有这样反复沉浸和剥离,才能慢慢找到自己的平衡点。不然久而久之,人就变成木偶,没有烟火气,也没有温度。
有人问,现在主旋律作品怎么吸引年轻观众?其实很简单,你别端架子,多一点真实少一点套路就够。《浴血荣光》播出后弹幕刷屏,“他出来了天就晴”,还有网友改编歌词唱“雨一直下,我等主席发话”。创作者看到这些花样表达,比奖杯证书更开心,因为知道自己努力没白费(B站弹幕数据2024.5月统计)。

去年年底,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交响音乐会》,轮到王仁君主持环节。他台下一直搓手掌,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朗诵课现场。一句“中国共产党”脱口而出的时候,自豪感涌起来,比领奖那阵还激动。据他说,这感觉不是装出来,是多年扮演与体验后的自然反应——角色已经渗透进生活,无论去哪儿,都甩不开影子似的跟着走。(现场音频由组委会授权)
至于未来呢?没人知道第六次相遇是什么模样,只知道五度春秋已足够刻骨铭心。或许哪一天再走进军博,又或者只是街角买菜遇见熟悉乡音,都可能突然想起那些黑白照片背后的故事,还有那个总爱拂蜘蛛网、嘴角挂笑意的人物剪影……

内容来自公开资料与个人见解,仅供学习交流,不构成定论或权威史实参考。

部分信源: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访谈、《瑞金县志》(1987)、江西省档案馆口述材料整理、《湖南方言志·湘潭卷》。
安联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